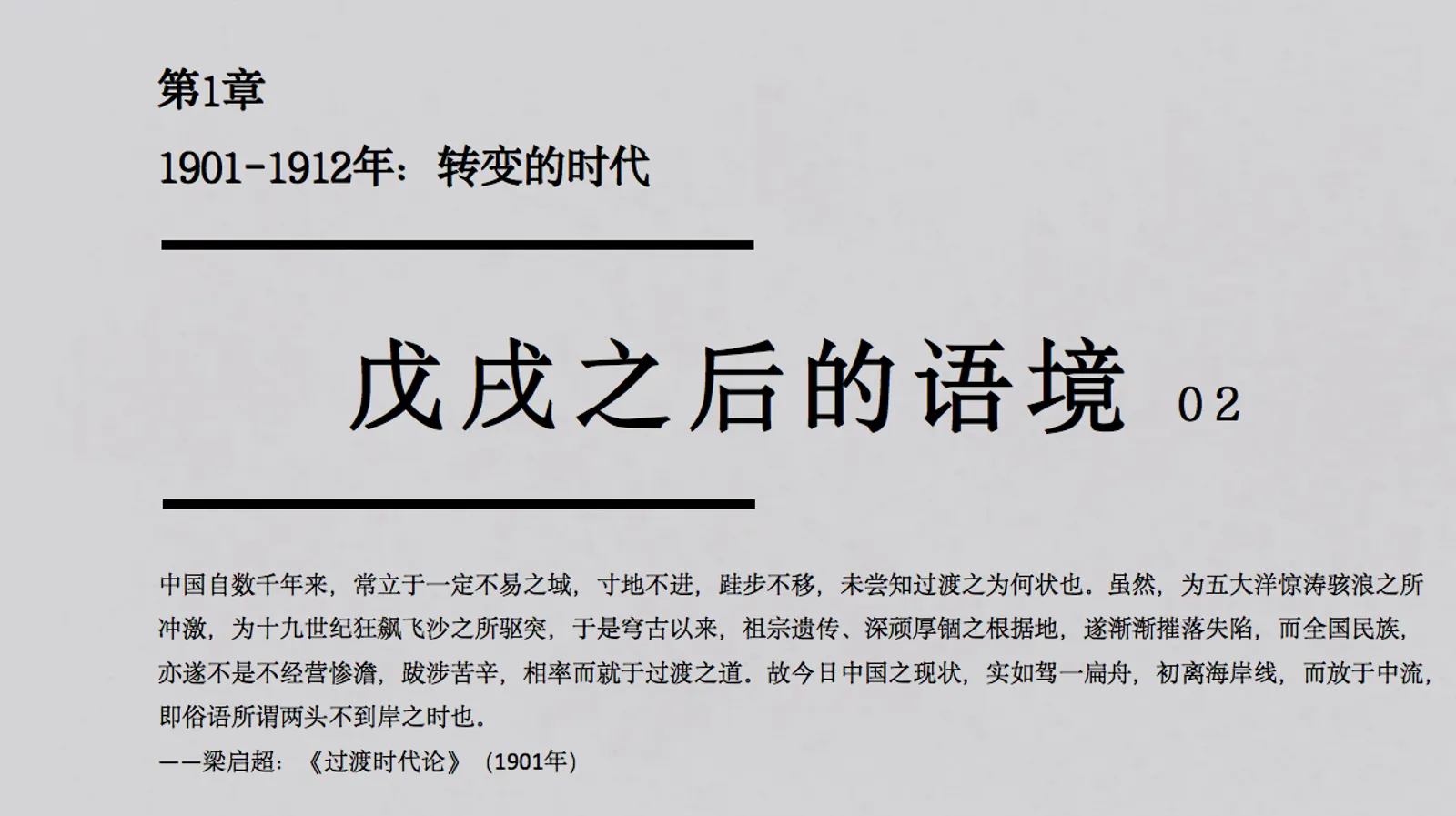
1901年到1904年间中国面临的困境继续深重,《辛丑条约》之后,日本威胁暂时消除,俄国于1900年7月借帮助清政府镇压义和团对东三省的占领按要求应该退出。但是,俄国显然欺负中国的衰弱,反而索要新的特权,1901年2月16日,俄国甚至提出新的条约,要中国支付占领费、铁路公司损失费,甚至代修一条从中东铁路向北京方向的铁路。1902年,清政府又与俄国签署《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沙俄军队分三期撤出中国。俄国没有撤出,反而在旅顺设立远东都督府并重新占领奉天(沈阳),与之同时,日、英、德、意等国因自己的利益警告中国不得单独与俄国签约,于是中国的舆论反过来要求中国加入日英同盟,对付俄国,清政府(李鸿章充当代表)在列强之间和清廷内部分歧中焦头烂额难以作为。1903年11月,英军进攻西藏地区;1902 - 1903年,英、美、日先后与中国签订《通商航行条约》,规定华商在各处设厂须与洋商在通商口岸设厂一样,向海关缴纳“出厂税”;1904年8月,德国兵舰驶入江西;1905年,俄国在与日本作战的同时进入新疆的喀什噶尔和伊犁。列强涉及领土、铁路、矿山和其他资源的掠夺,都逼迫中国必须有更加适应变化的应对措施,总理衙门被改为外务部,增设商部,都是适应形势的改变。但是,琐碎的措施仿佛来不及去填补由于制度上的缺陷而造成的迟缓和不可避免的错误,危机重重的现实激化了那些强调必须有政治上革新的人:经过戊戌维新的启蒙,人们将政治制度上的改革视为当务之急,维新运动渐渐转而进入立宪运动阶段。

1901年6月7日,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立宪法议》,对立宪政治制度进行了清楚的介绍:
世界之政有二种:一曰有宪法之政(亦名立宪之政),二曰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采一定之政治以治国民谓之政体。世界之政体有三种:一曰君主专制政体,二曰君主立宪政体,三曰民主立宪政体。
⋯⋯
宪法者何物也?立万世不易之宪典,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者也。
⋯⋯
立宪政体亦名为有限权之政体,专制政体亦名为无限权之政体。有限权云者,君有君之权,权有限;官有官之权,权有限;民有民之权,权有限。故各国宪法,皆首言君主统治之大权及皇位继袭之典例,明君之权限也;次言政府及地方政治之职分,明官之权限也;次言议会职分及人民自由之事件,明民之权限也。
⋯⋯
抑今日之世界,实专制、立宪两政体新陈嬗代之时也。按之公理,凡两种反比例之事物嬗代必有争,争则旧者必败而新者必胜。故地球各国,必一切同归于立宪而后已,此理势所必至也。[1]
将立宪政治提出来,使梁启超与之前那些基于自强运动和对儒家思想进行简单改造的精英人物例如张之洞,包括康有为明显地区别开来。在梁启超看来,社会变革根本就不能对专制制度有任何依赖,而张之洞主张“自强”的唯一目的是为了维护稳定这个集权专制的清政府(张的国家概念);至于康有为,他津津乐道于作为帝师的身份,他希望通过对皇帝资源的操纵,改变朝廷内部的权力结构——例如让那些具有维新思想的人掌握权力——来实现改革的目的。梁启超在政治的思考上走得更远,既然清政府对维新人士的镇压已经到了悬赏人头的程度,逼迫维新人士逃亡日本,这显然刺激了梁以及其他激进人士的变革步伐。
在日本,梁启超的确与革命家孙中山讨论过合作,尽管他们之间在政治与拯救中国的路径上看法有所不同,但是,梁启超一开始理解革命的动机与目的,他对共和政体也是认同的,但是基于中国需要开启民智,从中国国情的角度上看,他主张保持一种有序的政治策略。所以一开始梁启超就根据日本的经验给出了实现宪政的推进流程:
一、 首请皇上涣降明诏,普告臣民,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帝国,万世不替。
次二、宜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同异得失,何者宜于中国,何者当增,何者当弃。⋯⋯
次三、所派之员既归,即当开一立法局于官中,草定宪法,随时进呈御览。
次四、各国宪法原文及解释宪法之名著,当由立法局译出颁布天下,使国民咸知其来由,亦得增长学识,以为献替之助。
次五、草稿既成,未即以为定本,先颁之于官报局,令全国士民皆得辩难讨论,或著书,或登新闻纸,或演说,或上书于立法局,逐条析辩,如是者五年或十年,然后损益制定之。定本既颁,则以后非经全国人投票,不得擅行更改宪法。
次六、自下诏定政体之日始,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2]
次年,梁启超又写出《论立法权》,对“立法”“行法”以及“司法”三权分立进行了阐释,孟德斯鸠和边沁关于法与政治的理论被作为新知给予介绍。梁对孟德斯鸠(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Montesquieu,1689-1755)拥有不少知识领域的好奇心并不在意,而是关注这位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法的精神》(1748年)里关于立宪政治的分权思想[3]。实际上,一整套欧洲历史和思想语境支撑着孟德斯鸠的思想逻辑,例如法律是“导源于事物本质的必然关系”,法存在于自然与人类社会之中,这要解释上帝的创造与人类社会的法的关系,而启蒙时期要解决的是人类社会本身的法律问题。但是,梁启超忽略这些欧洲社会的思想与历史背景,他关注的是将孟德斯鸠的立法与行政分离开来的解释,他清楚,在中国的思想史上是找不出针对君主的权力究竟该如何从天的意志这一不能确证的状况到实际的合法性的解释的——儒家那一套国家逻辑例如君臣父子的关系与建立分权的宪政无法对接,尽管古代经典有过涉及民主色彩的文字,例如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是,古代经典中不多的这类思想完全没有制度上的安排,仅仅限于道德训诫。在《论立法权》(1902年)里,梁启超要给中国人——当然包括那些朝廷命官——解释:
立法、行法、司法,诸权分立,在欧美日本,既成陈言,妇孺尽解矣。然吾中国立国数千年,于此等政学原理,尚未有发明之者。[4]
梁启超将古希腊、罗马直至18世纪的关于立法权独立于君主帝王的欧洲历史,与中国古代无立法之历史进行了比较,想说由于缺乏随时代变迁需要的立法——“秦之距今,二千年矣,而法则犹是”,致使“君相既因循苟且,惮于改措,复见识隘陋,不能远图;民间则不在其位,莫敢代谋。如涂附涂,日复一日,此真中国特有之现象,而腐败之根原所从出也”,梁启超在这里说的正是“秦汉政体”一直持续到这时的根本特征。梁希望强调:中国古代的君主帝王是典型的专制主义者,他们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法者,甚至也是对执法对错的判定者。君主一个人可以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随时立法与毁法,只有君主的念头与奇想在运行一个国家,这样的结果是,古代圣人所规定的任何道德与品格要求,仅仅从属于君主或者行使君主意志的人的个人裁决。以致,当一个君主具有相对正常的心智、必不可少的历史知识以及人们可以接受的人性,加上具有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崇敬心时,他的言行才会有助于国家的运行,如果出现偏差,就要看有什么偶然的因素能够对错误给予修正与弥补。然而依赖偶然性是非常不可靠的,何况君王会因私欲难免对“天意”——“天意”当然是历代帝王的一个获得合法性的托词——产生偏于个人的理解。在孟德斯鸠看来,专制政府一开始就没有什么正当性,因为君主的意志与行为不遵循任何稳定的法律规则,专制政体容易产生政变和不稳定的动荡盖出于此,因此,孟德斯鸠关注权力在政府实施过程中的正确方式。梁启超引述孟德斯鸠的推论逻辑:一个人,或者一个部门兼有立法权和行法权,那么他或者部门如果既立苛法又行使苛法,例如既立夺人之财产法又行使权力没收他人的财产,这让任何人都无可奈何。所以,专制政体缺乏美德、荣誉、雄心,只有顺从、阴谋和恐惧,人人只能唯唯诺诺或者按照君主的意志(即便是来自天的命令,所谓“奉天承运”)行事。孟德斯鸠讨论了共和制和君主制,前者是少数人或多数人依法而治;后者是一个人依法而治,既然依法——宪法、法律以及基于宪法的其他规则——而治,就既可以保证君主稳定的地位,又具有获得民意的正当性。可是谁是立法者?梁启超借用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的思想告知人们:“多数之国民。”作为一位功利主义者,边沁坚信:只有导致多数人最大幸福的行动才是最好的行动。梁启超提示说:服从君主意志的专制政府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国家意志实际上是君主的意志,个人是没有可能导致他人或者多数人的幸福的,只有多数人选出来的代表,照顾到更多人的意志,所制定出来的法律制度才有可能产生更多的人的幸福。这样的理论在过去的中国没有人考虑过,例如,在政治实践上,如何理解存在着为他人的幸福所产生的个人付出!无论如何,梁启超的重点是否认国家作为君主的私产,而实为“一国人之公产”,既然如此,对公产的安排当然由多数国人的意志来确定,那么,作为个体的君主就没有权力成为立法的主体,否则最终国家“不可以立优胜劣败之世界”。在这里,梁启超将严复的告诫结合进了如何才能在竞争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政治安排中。同时,边沁的任何道德立场都可以用功利主义的方式(边沁将其表述为“幸福微积分”)来论证的思想也就悄悄地替换了含糊不清并且经常成为专制托词的儒家道德论——君主的任何承诺和道德声明都不能够成为正当性的依据,因为那些承诺与声明无法被计算,即人们无法得出作为个体的君主意志的立法或决策所导致的幸福是否大于痛苦,或者说由此所付出的成本是否低于收益,民主政治也就是被功利主义这样推导出来的,幸福是目的,民主是手段,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是君主的荣耀和收益(如果用边沁主义的术语来评估的话),梁启超就是这样试图在理论上推倒君主专制制度,而倡导君主立宪政治的。
报纸出版物涉及立宪政治这个主题的文章自1902年始越发密集,媒体发现,“当世君子”早上晚上都在讨论立宪问题;1903年,《大公报》开始发表有关立宪政治的文章,例如《论中国之立宪要义》:这一年,柳亚子以“亚卢”的名义在《江苏》(第6期)上发表《中国立宪问题》,用词极为急促:“遍四万万人中所谓开通志士者,莫不喘且走以呼吁于海内外日:立宪!立宪!!立宪!!!”[5] 这个时期,立宪的呼声远远高于革命。
在梁之前,有不少人涉及过西方政治,梁廷枏介绍美国政治,徐继畬介绍英国议会与司法制度,郑观应介绍西方议院,以后是立宪派在自己的媒体《时务报》上开始了政党政治的讨论,同时《国闻报》《湘学报》也是介绍西方党会观念的重要媒体。《时务报》第三册里告诉读者美国分有合众与共和两党,“各愿举其党人以任斯职”。在第四九册里,有这样引述翻译自《大日本杂志》的《政党论》里关于政党与立宪政治关系的说明:
政党之于立宪政治,犹如鸟有双翼。非有立宪之时,则政党不能兴;若立宪之政无政党兴起,亦犹鸟之无翼耳。[6]
而早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六月,严复就在发表于《国闻报》的《论中国分党》中讨论过西方政党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朋党会社:
中国之所谓党者,其始由于意气之私,其继成为报复之事,其终则君子败而小人胜,而国亦随之。其党也均以事势成之,不必以学识成之也,故终有一败而不能并存。西人之党则各有所学,即各有所见,既各有所见,则无事之时足以相安,及有所藉手,则不能不各行其意,而有所争于其间。其所执者两是则足以并立,而不能相灭。[7]
以后,梁启超及其同仁在《新民丛报》里不断发表有关政党政治的文章,尽管梁启超在对待自己的组织例如政闻社是否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政党性质仍然非常慎重,但是,努力推动立宪政治和政党建立的确是立宪派人士的目标[8]。在理解并传播西方代议政治和政党理论方面,革命人士是有所受惠的,只是他们与立宪派对政党的理解有所不同。基于立宪派的宣传与工作,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立宪的声音更为人们所关注,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华人圈子,结果,“维新派”一词为“立宪派”所替代。
注释:
[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第一册。转引自《梁启超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340-341页。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第一册。转引自《梁启超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340-341页。
[3] 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里另一个重点是讨论气候对风俗、道德与政府形式的影响,看来梁启超对这样的分析主题没有兴趣,此时的梁启超正在急促地寻找改变中国人政治观念的路径和方法,似乎来不及去细细思考中国的气候地理对这个国家的历史与制度的影响。
[4] 梁启超:《梁启超自选》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342页。
[5] 转引自高放等著:《清末立宪史》华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
[6] 转引自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页。
[7] 原载六月十三、十四日《国闻报》,转引自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34页。
[8] 梁启超在他的《政闻社宣言书》(1907年)里做了一个慎重的解释:“问者曰:政闻社其即今世立宪国之所谓政党乎?曰,是固所愿望,而今则未敢云也。凡以政党之立,必举国中贤才之同志主义者,尽网罗而结合之,夫然后能行政党之实,而可以不辱政党之名。今政闻社以区区少数之人,经始以相结集,国中先达之彦,后起之秀,其怀抱政治的热心,而富于政治上之知识与能力者,尚多未与闻,何足以称政党。”(梁启超:《梁启超自述:1873-1929》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359页。)